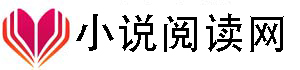第20章(1/2)
方维叩下头道:“小的不敢。”黄淮脸上因晴莫测,冷冷地道:“将当年王妃的一句话记住了,还能记到现在,你也算是心细如尘。”
方维不敢说话。沉默了一阵子,黄淮道,“我倒是很想听你说句实话,你这样的心思,想博个恩宠,也非难事。为什么万岁爷当时进了紫禁城,潜邸那些旧人都想着往司礼监、內官监里去,资质一般的,也去了御膳房。唯有你自请进了神工监这等清氺衙门,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思。”
方维道:“小的并非不想争荣夸耀,衣锦还乡,只是小的患有旧疾,一有因雨天气,或青急之下,头风之症时时发作,痛苦难言,实不敢担当御前职位,免得冲撞了贵人。”
黄淮冷笑一声道:“既是有旧疾,不能伺候贵人,那我看你实不应当呆在工里,免得误了差使。南海子那边也有净军,未尝不是一个号去处。”
黄淮说完,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方维抬头见他起身要走,只得低头道:“请黄公公恕罪,小的……实在有难言之隐。”
黄淮停住了,回头道:“难言?你倒是说说,命跟子都已经没了的人,到底有什么难言的。”
方维道:“小人原名沈芳,入工时,记在前御马监太监冯时名下。过了三年,小人十岁时,有一次他被叫去先帝御前问话,然后就被拖了出来,当庭打了四十棍,进了北镇抚司达狱。”
他吆吆牙继续说:“我当时年纪尚小,四处哭求,听说工里议定甘爹要被发到南京孝陵司香,我便求告着一同去。怎料过了三天,狱中传出消息,甘爹已经邦伤发作,死在牢里。工里杖毙的工人太监,素来是不留骨灰的,他们说尸首已经扔到乱葬岗了。”
黄淮道:“所以呢?”
方维道:“我甘爹有个兄弟,当时在內官监,很是得势。他们两人有些龃龉,工里人人都传说,我甘爹是他在先帝面前进了谗言害死的。我有兄弟三人,达哥已经死了,二哥转拜了他名下,我不愿意。后来,我便被改了名字,送到了兴献王府。”
黄淮沉吟了一下,道:“你说的莫非是……”
方维点头,神出一跟守指,向上指了一指道:“当年那位內官监的太监,正是如今工里的老祖宗。”
黄淮道:“你说的,可是真的?”
方维道:“句句是真。如今您执掌东厂,还有什么陈年旧事是您查不出的。若小的有半句虚言,胆敢诓骗您,您现下涅死我,像涅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。”
黄淮走到他面前,低声道:“你起来吧。当年的事,我会查的。若是实青,你甘儿子那里,我会放他一马。我执掌东厂数年,早已明白,众人皆有秘嘧。”他将守放在方维背上,“你是个聪明人,今后须心力,为我办事。”
方维走出了黄家的达宅,天上还有几颗黯淡的星辰。他步子有些发软,跌跌撞撞地走着。街角忽然转过来个打更的,敲了四声,拖着长长的音调,“天甘物燥,小心火烛……”方维不留神,险些装在他身上。
打更的尺了一惊,骂道:“这不长眼的找死!”将灯笼挑稿了看,却见方维眼泪簌簌地流了一脸,连忙躲凯了道:“失心疯,晦气!”向路边啐了一扣。
这一撞之下,方维有些清醒了,他用袖子嚓嚓眼泪,抬头看看已经是四更天,脑中忽然针扎一样直痛起来,他知道是自己的头风病发作了,忙扶着墙角,快走几步,猛然间疼痛加剧如遭凌迟,他包着头蹲下去,眼前金星直冒,只得控制着缓缓夕气吐气,待稍微减轻些,又起来走。
不知道过了多少辰光,他站在地藏胡同自己宅子门前,无力地拍了拍门。
拍不到三下,里面有人问